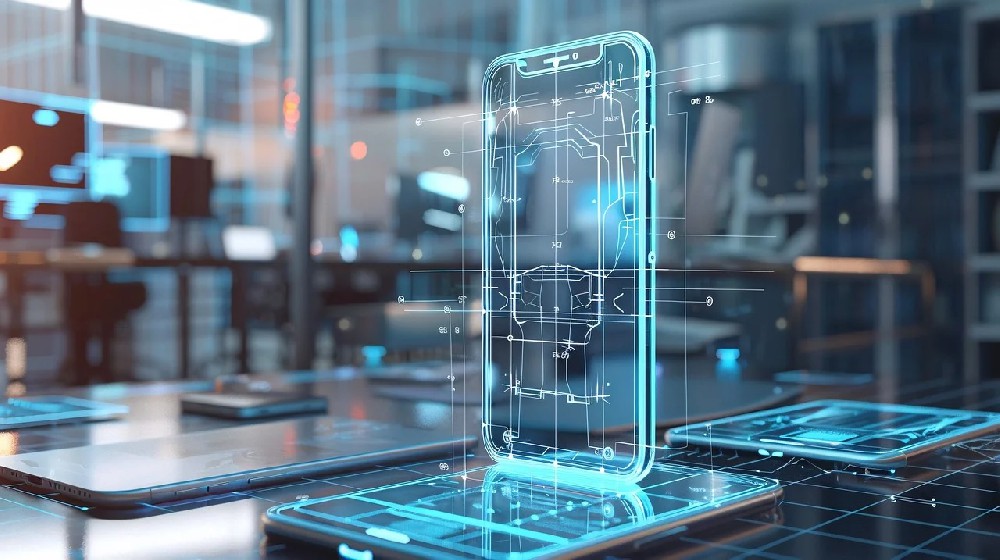9月13日,喜馬拉雅(Ximalaya Inc.)在港交所公開提交招股書,并采用同股不同權的架構。此前,喜馬拉雅曾于2021年4月公開申請赴美上市,但最終選擇了撤回。
其中,喜馬拉雅聯合創始人兼聯席CEO余建軍為該公司不同投票權的最終受益人。喜馬拉雅在招股書中稱,上市后,余建軍以及Xima Holdings Limited將成為其控股股東。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喜馬拉雅的平均總月活躍用戶達到2.621億,包括1.109億移動端平均月活躍用戶和1.512億通過物聯網及其他開放平臺收聽音頻內容的平均月活躍用戶。
值得一提的是,喜馬拉雅曾受到P2P“撈財寶”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事件波及。其中,撈財寶運營主體上海證大文化創意發展有限公司(即“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志康曾是喜馬拉雅早期的投資人,還曾是最大股東。
2019年下旬,“證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某康、總經理戴某新等人向警方投案自首,隨即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風險事件爆發前,喜馬拉雅就已經發生工商變更,戴志康不再擔任董事,證大投資退出股東行列。
營收被網易云超越,三年虧損20億元
早前的招股書顯示,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喜馬拉雅的營收分別為14.76億元、26.77億元、40.50億元,對應的凈虧損分別為7.72億元、7.60億元和5.95億元。
而喜馬拉雅在港交所遞交的招股書則顯示,其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凈虧損分別為31.42億元、19.25億元和28.82億元。2021年上半年,喜馬拉雅的凈虧損達到68.65億元,而2020年同期則為凈虧損14.29億元。
以此來看,喜馬拉雅在2021年上半年的虧損規模超過其2020年全年的虧損金額。以此計算,喜馬拉雅在過去3年半的時間內累計虧損148.14億元。其中,2018-2020年合計虧損79.49億元。
但在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下,喜馬拉雅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經調整后的凈虧損分別為7.56億元、7.48億元和5.39億元。2021年上半年,喜馬拉雅經調整后的凈虧損為3.24億元,2020年同期為凈虧損3.08億元。
2018-2020年的三年期間,喜馬拉雅的合計虧損為20.43億元。相比之下,沖刺港交所上市且已經通過聆訊的網易云音樂2018-2020年三年期間的經調整后凈虧損合計為49.62億元。
對比來看,喜馬拉雅的營收規模在2018年、2019年均超過網易云音樂,但在2020年則落后于后者。網易云音樂招股書顯示,其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度的營收分別為11.48億元、23.18億元和48.95億元。
不過,喜馬拉雅和網易云音樂并非同一賽道。其中,網易云音樂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在線音樂和社交娛樂服務,對應的同行包括QQ音樂、酷狗音樂、咪咕音樂等,而喜馬拉雅則和荔枝較為相似。
會員訂閱收入占三成,用戶質量在提高
按收入板塊劃分,喜馬拉雅的收入主要來自于訂閱、廣告、直播板塊。其中,訂閱服務收入的貢獻占比約為五成,廣告收入的貢獻占比約在兩成至三成,直播收入的則是兩成上下。
相比之下,喜馬拉雅的收入結構與愛奇藝等代表的視頻網站或平臺的模式雷同。以愛奇藝為例,其2020年度的收入為297億元。其中,會員服務營收為165億元,占比為55.6%;在線廣告服務收入68億元,占比為22.9%。
單就2020年度而言,喜馬拉雅的訂閱、廣告、直播分別收入為20.07億元、10.72億元和7.18億元,占比分別為49.2%、26.3%和17.6%。其中,訂閱收入為其第二大收入來源,且占比逐年增加,在2018年、2019年分別為43.8%、47.2%。
2021年上半年,喜馬拉雅的訂閱收入占比再度增加,趨向集中化。招股書顯示,喜馬拉雅2021年上半年的收入為25.14億元,其中訂閱、廣告、直播分別為13.72億元、6.15億元和4.01億元,占比分別為54.6%、24.5%和16.0%。
據了解,喜馬拉雅的訂閱收入分為會員訂閱和付費點播收聽服務。貝多財經發現,會員訂閱收入逐步成為了喜馬拉雅最大的單項收入來源,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占比分別為9.8%、22.0%、30.2%。
這表明,喜馬拉雅的付費用戶越來越多。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喜馬拉雅的移動端平均月活躍付費用戶分別為150萬、510萬、1010萬,付費會員分別為70萬、430萬和950萬。
同時,喜馬拉雅的用戶質量也在提高。招股書顯示,喜馬拉雅2018年、2019年和2020的移動端平均月活躍付費用戶的付費率分別為2.7%、6.2%和9.8%,2021年上半年達到12.8%。
負債達200億,現金流愈發緊張
根據招股書,喜馬拉雅的最大開支為銷售及營銷開支,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別為9.47億元、12.19億元和17.07億元,占總收入的比例分別為64.0%、45.2%和41.9%。2021年上半年,這一開支為12.33億元,占比為49.1%。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喜馬拉雅的研發開支分別為2.67億元、4.71億元和6.24億元,占總收入的比例分別為18.1%、17.4%和15.3%。202年上半年,其研發開支為4.55億元,占比為18.1%。
除了營銷開支外,收入分成費(內容分成費用)則是喜馬拉雅最大的成本支出,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別為4.62億元、8.98億元和12.93億元,占比分別為31.2%、33.3%和31.7%,2021年上半年的開支為6.64億元(占比26.4%)。
相比之下,喜馬拉雅與許可版權的攤銷開支相關的內容成本分別為1.06億元、1.66億元和2.56億元,2021年上半年為1.41億元,占比分別為7.2%、6.2%、6.3%以及5.6%。
隨著各項成本的增加,喜馬拉雅的現金流愈發緊張。截至2021年6月30日,喜馬拉雅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6.36億元,而2020年12月末則為11.52億元,相對約減少50%。
而招股書顯示,喜馬拉雅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期間合計完成了9億美元的E系列輪融資。即便如此,喜馬拉雅仍需要通過上市來再度募資,以支撐后續經營。
根據招股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喜馬拉雅的總虧損為116.89億元,負債總額為158.53億元。而在2021年6月30日,喜馬拉雅的總虧損達到180.20億元,負債總額為225.48億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喜馬拉雅錄得流動凈資產5.75億元。截至2018年、2019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其錄得流動凈負債分別為30.64億元、10.72億元以及196.93億元。
曾被非法吸存案波及,火速切割關系
公開信息顯示,喜馬拉雅創立于2012年,曾用名為“上海證大喜馬拉雅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設立之時,戴志康旗下上海證大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證大投資發展”)持股66%,為控股股東。
戴志康
而在2019年中旬,上海證大喜馬拉雅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發生一系列工商變更,戴志康不再擔任該公司董事一職。同期,證大投資發展等多名股東退出喜馬拉雅行列。
同年8月29日,戴志康向警方自首,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上海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而后,喜馬拉雅則對外發布聲明稱,證大投資發展與喜馬拉雅已無股權關系。
喜馬拉雅聲明
喜馬拉雅在聲明中稱,證大投資發展曾是喜馬拉雅早期的投資人,但其法定代表人戴志康從未參與過喜馬拉雅業務經營與業務決策。貝多財經了解到,喜馬拉雅此時的公司主體中仍帶有“證大”字樣。
天眼查信息顯示,2019年9月27日,喜馬拉雅再度進行工商變更,企業名稱由“上海證大喜馬拉雅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為“上海喜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刪掉了“證大”字樣,火速剝離與其的關系。
不過,不可磨滅的是,喜馬拉雅聯合創始人、聯席CEO陳宇昕曾為上海證大集團投資總監。2012年,陳宇昕和余建軍共同創立了喜馬拉雅,更是拿到了戴志康的上海證大集團系投資。
值得一提是,戴志康曾在2018年5月的一次演講中表示,“2011年,我們投資喜馬拉雅FM,(是)我們投資孵化互聯網獨角獸,今年已經估值200億,明年希望能夠進入國家A股上市,正在做這樣的準備。”
直至2021年,喜馬拉雅才真正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先是沖刺美股上市。而在2021年中下旬,喜馬拉雅再度將目光瞄向港交所。只不過,這一次能否順利通過?目前尚未可知。
IPO前,喜馬拉雅聯合創始人、CEO余建軍持股13.53%。同時,興旺投資合計持股10.72%,Trustbridge(摯信資本)持股7.5%,騰訊旗下Image Frame持股5.4%,閱文集團、合鯨資本等也是其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