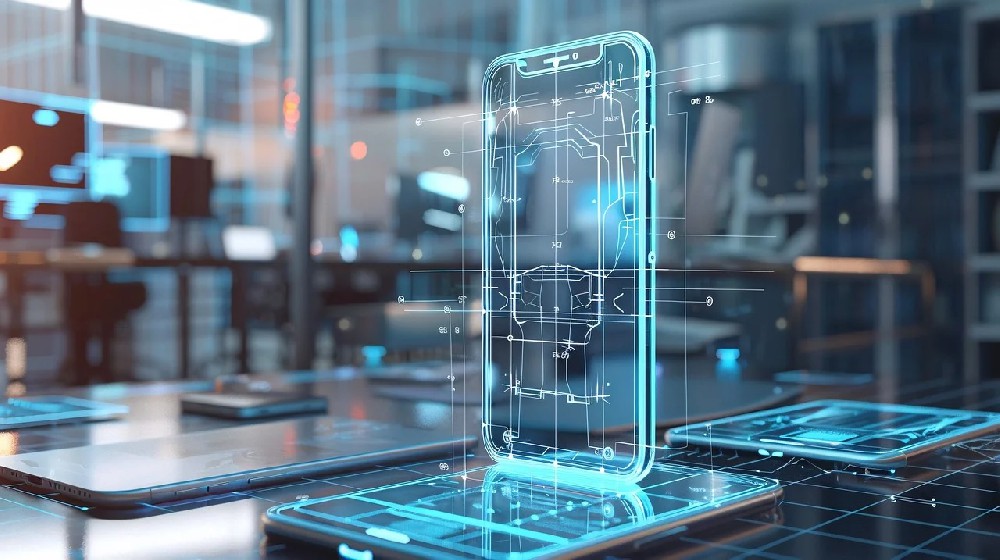撰稿|何威
來源|貝多財經
從管理超過4500億的基金規模,到徹底歸零需要多長時間?
華夏基金“ETF一哥”張弘弢告訴我們只需要4個多月。

隨著最后2只公募產品的基金經理卸任,曾經的“華夏ETF一哥”已無在管公募產品。
4月19日,華夏基金公告稱,因個人原因,張弘弢卸任華夏中證紅利質量ETF及其聯接基金的基金經理,離任日期為4月17日。這也是繼去年11月后,他再次卸任產品,自此,張弘弢已無在管公募產品。

而張弘弢離職的背后,華夏基金后繼無人、ETF龍頭位置不保,主動權益類效益不佳,內部風控等問題都浮出水面。
一、人才凋零,后繼無人
隨著張弘弢的卸任,他超過15年的公募基金經理職業生涯也隨之畫上了一個階段性的句號。
自2000年4月起,他便加入了華夏基金,自2009年起開始掌管其首個公募產品——華夏滬深300指數基金。
自2012年起,張弘弢管理的公募產品數量逐漸增加,涵蓋了QDII被動指數型股票基金、偏債混合型基金、混合債券型二級基金、增強指數型基金以及靈活配置型基金等多種不同類別。
在被動指數型基金領域,除了前述的華夏滬深300指數基金(現更名為華夏滬深300聯接基金),華夏上證50ETF、華夏科創50ETF等華夏基金旗下的大型ETF產品也曾由他擔任基金經理。
在2020年第四季度市場熱度高漲的背景下,公募行業誕生了首批三位管理規模突破千億元的基金經理,張弘弢便是其中之一。
隨后,隨著指數化投資的興起,華夏基金旗下的ETF產品管理規模迅速增長,張弘弢作為管理多只大型ETF產品的基金經理,被譽為公司的“ETF一哥”。在他的管理下,產品規模曾連續多個季度位居非貨幣市場公募基金經理之首。
根據定期報告的數據,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張弘弢管理的資產規模達到4561.44億元,位居市場第十位。
但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華夏ETF規模雖然穩居行業第一,但部分產品卻深陷“規模越大、虧損越重”的陷阱。
其中,張弘弢管理的華夏科創板50ETF聯接A任職期間回報率為-22.40%;華夏科創50ETF任職期間回報率-29.93%,大幅跑輸同類平均水平,導致基民持有期累計虧損超328億元。

來源:天天基金網
而張弘弢的離任,也暴露出華夏基金在被動投資領域的人才儲備短板。接任者楊斯琪雖具備10年從業經驗,但管理超500億元規模產品的履歷尚屬空白,進一步加劇了市場對其投研團隊穩定性的擔憂。
之前華夏基金最著名的基金經理非王亞偉莫屬。在2005年12月至2012年5月期間,王亞偉管理的“華夏大盤精選”基金復權單位凈值增長率高達1198.91%,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達到1046.05%。自那時起,“公募一哥”的稱號便與王亞偉緊密相連。
但王亞偉在2012年4月離開華夏基金,轉而投身私募領域,并創立了千合資本。緊隨其后,范勇宏也離開了華夏基金,而江暉、石波、張益馳、孫建冬等資深基金經理也紛紛轉戰私募行業。
隨著資深基金經理團隊的相繼離開,華夏基金遭遇了人才流失的困境,新生代基金經理的表現難以與前輩們相提并論。
近年來,“能源一哥”鄭澤鴻于2016年加入華夏基金,他管理的華夏能源革新股票基金因精準布局新能源領域,在2021年一季度末以226億元的規模成為市場上最大的新能源主題基金。
然而,到了2024年7月,鄭澤鴻卻選擇了清倉式卸任。除此之外,華夏基金的“科技名將”周克平也在3月對其管理的所有產品進行了清倉式離任。

來源:天天基金網
周克平是華夏基金從零開始培養的基金經理,因其在科技板塊的專注,華夏基金曾賦予他“科技名將”的稱號。
二、業務前后夾擊
除了核心人物的卸任引起業界的廣泛關注外,華夏基金無論是在被動權益類還是主動權益業務基金方面,均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壓力。
據中信證券年報顯示,華夏基金全年營收達到80.31億元,同比增長9.61%,凈利潤為21.58億元,同比增長7.20%,管理規模已突破2.46萬億元。
然而,這一增長主要依賴于被動投資的擴張,而該領域目前正面臨巨大的挑戰。
在2024年,基金行業經歷了一場激烈的ETF發行競爭,眾多知名公募基金公司不惜投入巨資,采取低價策略以吸引投資者,這無疑加劇了華夏基金在ETF業務領域的競爭態勢。目前,ETF市場已演變為競爭激烈的紅海。
諸如華泰柏瑞基金、南方基金、嘉實基金等領先的基金公司,紛紛推出新型ETF產品,并加強市場推廣活動。
盡管華夏基金在ETF領域曾居于領先地位,但其優勢目前正面臨嚴峻的挑戰。根據IFIND數據,截至2024年底,華夏基金的ETF資產規模接近6600億元,而易方達基金緊隨其后,規模達超過6000億元。

來源:IFIND
從資產規模的增長來看,易方達基金在2024年的ETF資產規模增長高達3294.43億元,超越華夏基金,成為資產規模增長最快的基金公司。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ETF領導地位的爭奪已進入白熱化階段。
在這一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華夏基金還遭遇了降費浪潮的沖擊。2024年,華夏基金多次宣布降低旗下基金的管理費率和托管費率。
例如,華夏上證50ETF、華夏上證科創板50成份ETF、華夏滬深300ETF等規模達千億級別的產品,其管理費年費率從0.50%降至0.15%,托管費年費率從0.1%降至0.05%,降幅分別達到70%和50%。這種以降低費率為主的應對策略,給華夏基金的盈利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而相比于被動權益類的艱難應對,主動權益業務的低迷已成為明顯的短板。
Choice數據顯示,2024年華夏基金權益類產品平均收益率僅為-18.72%,大幅低于同期偏股混合型基金-8.56%的平均水平。
其中,華夏優勢精選股票全年虧損33.12%,在746只同類產品中排名倒數第11;曾被寄予厚望的華夏智造升級混合A、華夏新起點混合C等產品跌幅均超30%。
2024年主動權益收益排名前50的產品中竟無華夏身影,與2023年“華夏北交所創新中小企業精選混合”摘得年度冠軍的盛況形成強烈反差。
同時,天天基金網顯示,華夏基金主動權益管理規模正經歷顯著收縮,股票型與混合型基金規模三年累計降幅均超四成。
截至2024年末,華夏基金主動權益類產品(含股票型、混合型)管理規模為3200億元,較2021年峰值縮水超1300億元。股票型基金規模從2021年末的434.19億元降至248.93億元,降幅42.67%;混合型基金規模從2102.07億元腰斬至1157.94億元,降幅達44.91%。

來源:天天基金網
在ETF規模競爭陷入紅海、主動權益又難出爆款的情況下,華夏基金亟需打破“被動強、主動弱”的失衡結構,否則可能面臨客戶流失與品牌溢價雙重損耗。
三、內部管理問題不少
要說這幾年華夏基金最大的問題,那當時2023年的“老鼠倉”事件,當時原基金經理夏云龍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實際控制的“張某”證券賬戶進行未公開信息交易,涉及華夏紅利混合型基金和華夏周期驅動混合型基金,最終被罰沒1061.56萬元。該案是繼2019年王鵬“零口供老鼠倉案”后,華夏基金再次因同類事件被重罰,反映出對投研人員交易行為的監控失效。
2023年因“夏云龍案”及“童汀違規交易案”,華夏基金被暫停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6個月,直接導致當年主動權益類產品規模縮水21%。
而到了2024年,在ETF規模宣傳、信息披露等環節多次遭監管關注。2024年在中證A500ETF推廣中,廣告使用“規模最大”表述(大字突出)。

來源:新浪財經
但實際僅限ETF領域,小字注釋被質疑存在誤導性陳述,違反《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銷機構監督管理辦法》。該事件引發監管問詢及輿論對“打擦邊球營銷”的批評。
與易方達、華泰柏瑞等競爭對手相比,華夏基金2024年因合規問題導致的業務停滯風險更高。例如,易方達同年ETF規模增長133.2%,而華夏因內控整改導致非貨ETF領先優勢從1200億縮窄至600億。除此之外,華夏基金在如基金清盤或重大虧損極端風險事件中,面對投資者投訴處理效率及賠償機制的有效性尚未被驗證。例如,華夏中證800指數增強基金2024年規模縮水45%,但未披露持有人集中投訴的解決方案。
華夏基金曾經站在時代的風口,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而現在同樣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展望2025年的發展道路,華夏基金需要時刻警惕風險,敏銳地洞察金融市場的新趨勢,并始終堅持風險控制的原則。
唯有如此,方能保持行業領頭羊的地位,建立持久且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長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