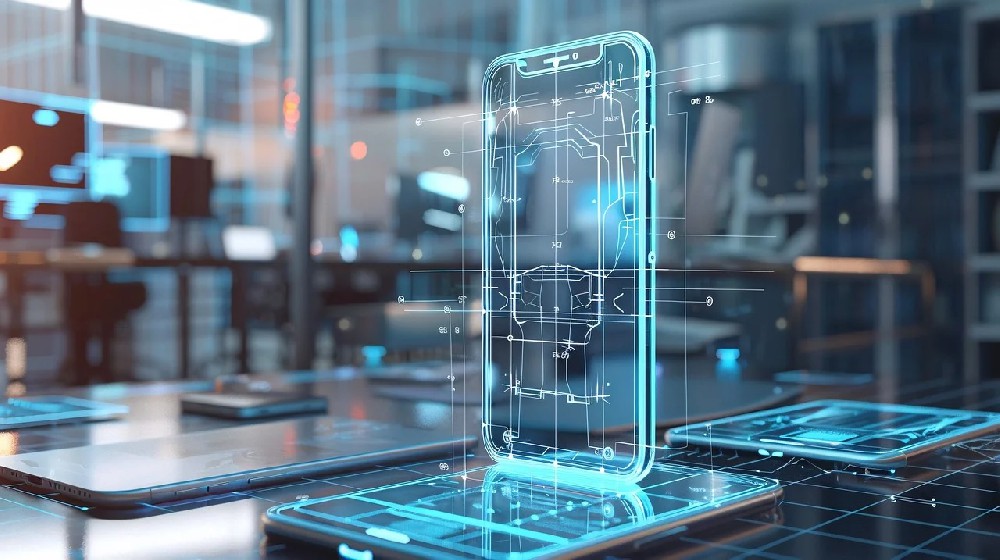曾經力超萬達,碾壓各大房企的地產“一哥”—綠地控股(600606.SH),日子過得尤為艱難。
一方面,近期綠地控股披露的2023年業績預告極為糟糕,出現了巨額虧損。預告數據顯示,預計2023年綠地控股實現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為-90億元到-70億元,與上年同期盈利10.10億元相比,將出現巨虧。預計歸母扣非損益后的凈利潤則為-94億元到-74 億元,而2022年這一數值是盈利18.52億元。
另一方面,綠地控股在資本市場表現也極其動蕩,股價持續低迷。截止4月12日收盤,其股價報收1.77元/股,創近15年來新低。按此計算,該公司的總市值僅約為249億元。
頂著內外壓力,綠地控股近期又陷入了“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的境遇。
據天眼查經營風險信息顯示,4月8日,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新增2則欠稅公告,欠稅稅種為城市維護建設稅、增值稅,欠稅余額分別為71.5萬余元、742.7萬余元。且該公司現存多條被執行人及股權凍結信息,被執行總金額超9.1億元。
當然,如今用房地產將綠地控股進行掛鉤,是有失偏頗的。畢竟早在2021年11月份之時,綠地已經做出了逃離地產行業的選擇,將公司所屬行業類別已由“房地產業”變更為“土木工程建筑業”,試圖轉換賽道尋求新增長。
但從如今面臨著巨額債務壓力,以及盈利能力堪憂的現實情況下,“換馬甲”求生的綠地控股,接下來所要做的事情仍有很多很多。
一、多元化轉型受阻,業績掉頭而下
據最新的2023年三季報顯示,綠地控股的股權結構中,以張玉良管理層為首的員工持股方代表——上海格林蘭持股比例為25.88%,代表上海國資委的上海地產與上海城投合計持股46.37%,剩余社會資本合計持有27.75%股份。上述股東中沒有任何一個股東能夠單獨對公司形成控制關系,該公司無控股股東。
可以說,綠地控股是有國企光環來加身的。但實際上,通過2020年的第二次混改,綠地控股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國資在這里只是充當一個財務投資者的角色,而該公司的實際經營權還是掌握在以張玉良為首的管理層手中。
缺乏明確的實際控制人,也間接地導致了綠地控股的發展陷入困境。由于沒有實控人的穩定領導,企業的發展戰略方向變得不夠明確和穩定,這可能導致了盲目的多元化擴張,從而加重了企業的財務負擔。
毫無疑問,2014年是綠地控股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當年銷售額高達2408億元,成功超越了萬科,坐穩了房地產行業的銷售冠軍頭把交椅。當年營收更是同比翻了近294倍,凈利潤翻了超79倍,一時間風頭無兩,也為第二年成功上市夯實了基礎。
在2015年上市后,綠地控股馬不停蹄進行了戰略調整,確立了“一主三大”戰略,即以房地產開發為主業,同時成立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費三大板塊,地產業務從規模導向轉為盈利導向。
客觀公允來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及時調整戰略的方式似乎更有前瞻性,也意義深遠,其邏輯很簡單,那就是希望通過板塊之間的協同效應,產生“1+3大于4”的效果。比如,在大基建領域,通過“地鐵+物業”綜合開發模式,推動地鐵項目大規模落地的同時綜合開發地鐵沿線物業產業。布局TOD不僅能夠使綠地集團以較低的價格、更容易的方式獲得土地,而且可以盤活集團自有的商業資源,提高商辦類物業租售率。
但萬萬沒想到,市場瞬息萬變,此次的戰略調整并不成功,也直接導致了整個公司業績的下滑,財務狀況開始一步步走向“深淵”。
比如,在第二次混改的2020年,綠地控股的凈利潤達到歷史以來最高值,為211.36億元,但隨后的兩年時間里,凈利潤一瀉千里,如股價一樣大“跳水”,到2022年末之時僅盈利45.97億元,相當于回到2014年的水平。
而銷售毛利率方面,地產板塊銷售毛利率長期保持在17%左右,但加入多元化業務之后的整體銷售毛利率卻只有7%;基建業務毛利率更是連5%都不到,并沒有地產業務賺錢。整體毛利率也從2019年的15.46%高位每年一路下行,到2022年末之時已降至10.5%。
而到了2023年,雖然全年的詳細業績還有待披露,但正如開篇提及的利潤巨虧預告,就足以說明去年綠地控股財務困境極大可能進一步加劇了。此外,我們也能從前不久綠地控股披露的兩則簡報中,窺見其當下面臨的巨大經營壓力:
2023年第四季度房地產經營情況簡報數據顯示,2023年1-12月,綠地控股完成新開工面積76.8萬平方米,同比減少46.0%;實現合同銷售面積1058.4萬平方米,降幅17.3%;實現合同銷售金額1114.69億元,同比下降15.8%;去年新增房地產項目儲備僅僅只有1個。
其基建業務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同期披露的基建業務經營情況簡報顯示,2023年綠地控股新增建筑施工項目總計4069個,總金額為2874.42億元,同比大幅減少40.89%。
不難看出,一方面僅占總營收45%的地產開發業務,在樓市寒冬的背景下,也沒能幫助公司提振多少利潤,反而還受連累被拖垮。另一方面,并不賺錢的基建業務也還在面臨慢慢萎縮的風險。兩大業務均陷入了兩難境地。
二、高企債務壓頂,如何破解?
事實上,綠地控股在地產領域的業務與自身其他多元化領域之間的協同作用相對有限。尤其是考慮到綠地另一核心業務—基建業務,它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流動來驅動,這就導致各個業務板塊之間存在錯綜復雜的資產與債務聯系。
在這種背景下,地產板塊往往扮演著為其他多元化業務提供資金支持的關鍵角色。簡而言之,房地產在綠地控股中起到了“金融輸血”的作用,以支持其他業務更好的發展。
身肩重任下,也意味著壓力就大,而為了增強自身的“輸血”能力,綠地控股開始在房地產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擴張。
就拿綠地控股最鐘情的在全國各地建立地標項目為例,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地標收割機”。從2005年450米高的南京紫峰大廈為開端,綠地控股后續在十多個城市開始瘋狂不惜砸重金加碼投入,在這些一二線城市里,都能找到綠地旗下的地標項目。比如,還未完工的在成都投資120億的最高樓項目“468”;中西部第一高樓,而如今被戲稱為“平頭哥”的武漢綠地中心等等。
然而,這種擴張策略導致各個業務板塊的負債率持續上升,居高不下。
實際上,綠地控股地產板塊的資產與負債規模早在2019年就分別達到了1.95萬億和1.75萬億,遠高于并表之后集團整體的1.14萬億和1.01萬億。
直到2023年第三季度末,綠地控股的總資產為1.19萬億元,但總負債高達1.03萬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86.24%,離資不抵債已越來越近了。
中指研究院發布《2024百強企業研究報告》顯示,2023年,百強企業剔除預收賬款的資產負債率均值為66.1%,綠地控股在去年三季度末時該指標已經高達81.13%;百強企業現金短債均值比為1.67倍,而綠地控股僅約為0.92倍。
更為危險的是,就在2023年7月份,綠地控股通過跨境擔保方式發行的境外債券“綠地集團 5.875% 2026-07-03”(債券代碼5769.HK)發生了付息違約,違約金額0.18億美元,這也是其首次發生債券實質性違約,這顯然不是一個好兆頭。
除此之外,綠地控股存續境外債券還有共計8只,本金余額共37.19億美元,分別將于2024年6月至2027年1月之間陸續到期。
但就目前綠地控股自身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能否正常兌付以上到期債券,也得打上一個問號。要知道,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綠地控股貨幣資金僅為401.95億元,但一年內到期的流動負債卻高達591.96億元,已無法完全實現覆蓋。
對此,早在去年7月份之時,穆迪就在其發布的評級報告中,將綠地控股家族評級從“Caa2”下調至“Ca”,并預計,鑒于綠地控股的高債務杠桿率和運營子公司層面的大量融資,在破產情況下,其離岸債券持有人的預期回收率將較低。
如今綠地控股的真實寫照,也正印證了一句古話:“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對于一個企業而言,也同樣如此。
綠地控股的命運,既有自我多元化轉型變革的失策,也有身處當下房地產市場大變局攪動下的無奈,接下來能否“活下去”,離黎明曙光更近,市場和時間會給出最終答案。